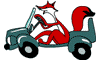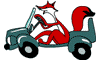|  |
 | | 山之颠 云之南 |
《交通世界》一兵文辛城图/一大堆金属用现代技术拼凑起来,再装上四个橡胶轮子——我的老伙计2020越野车又一次拉着我离家出走……
正是午饭时分,街角的小餐厅里依然冷清,背景音乐中播放着蔡依林演唱的歌曲《Don'tStop》,辛诚又一次点燃了香烟,刚刚驾车从西藏回来,他那古铜色的皮肤上依然挂着雪域高原的骄阳,不知是香烟熏的或其它什么原因,辛诚的眉毛和瞳孔突然紧缩起来,刹那间,一向庸懒疲惫的眼神中,精光一闪,提醒了人们对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瘦小汉子可千万不能小视。
“那你为什么又开着你那个破金属盒子离家出走了呢?”我笑着问。
辛诚不喝酒只喝茶,这对于海军陆战队和警察特勤出身的他来说,从概念上让人感觉有些出入。他端起茶杯,长长叹了口气,反问到:“哎!说什么好呢,整天憋屈在砖头做的盒子里,穿梭于浑浊不堪的空气和水泥丛林之间,面对着几十个用近似的腔调,雷同的节目宣传着同一个愿望,同一种生活方式的电视频道,你能忍受多久?”
“所以,这就是我要时不时驾车出去的原因,这几年我可真没少跑,光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我就上去过三次,穿越过阿里无人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和内蒙古大草原。”言语间,辛诚的黑脸上罩着不止一层的自豪。
“就讲讲这次吧,这次西藏之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是什么?”我指着餐厅外面辛诚的那辆心爱的座骑问。那是一辆墨绿色的陆迪(北京吉普有限公司在2020基础上改型的两门吉普车,由于生不逢时,据说投入了上亿元开发资金,仅生产了六十辆。),粗旷的外型,结实的项架和车身上四处刮蹭的痕迹,无不向人们召示着车主非凡的经历。
“易贡,这次举世罕见的泥石流就发生在那里,你知道,将近三亿立方米的沙石,在洪水的裹携下,从海拔5000米的高度以雷霆万均之势砸在海拔1000多米的易贡峡谷上,一瞬间,在易贡河上形成了一道两千多米高,两千多米宽的堤坝,将易贡河拦腰截断,想想吧,一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三米厚的泥沙石块从天而降,那是什么动静,什么气势!”说到这,辛诚有些激动,的确,如果此事发生的北京、上海、纽约、东京……想到这我也感到不寒而栗。
“这次越野探险活动我们的路线是从滇藏线经川藏线到达拉萨,再从拉萨经日喀则,协格尔,终点为珠穆朗玛峰大本营。那么,易贡河、通麦桥就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泥石流爆发后形成的堤坝,使得易贡湖水大量淤积,水位猛涨积水量达十几亿立方米,马上就要到达堤坝的顶端,强大的水压压迫着沙石堆积的坝体,随时有垮坝的可能。一旦垮坝,十几亿立方米的洪水将夹带着三亿立方米的沙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易贡下游所有的一切一扫而光。如果此时我们的吉普车队从此地经过,咱们恐怕只有来世再见了。所以,我们这次一出发就是顶着雷冒着险走的。”辛诚苦笑着继续说。
“就不能改变路线么?”我问
“哎!这年头,多数人的灵魂是装在少数人的钱袋子里的。”辛诚所答非所问地抱怨了一句,神色略显黯然。
“我们沿着茶马古道一直北上,经过中甸、德钦顺着澜沧江进入了西藏。海拔越来越高,沿途不时出现巍峨壮丽的雪山,当我们的车队翻过舒伯拉山,到达通麦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凉了,以前那水滔滔的易贡河断流了,涓细的泥汤像一条蜿蜒的小蛇,在裸露的巨大岩石间缓缓蠕动。天空阴霾,不时,一块沉掂掂的浓云飘过,把携带着的雨滴劈头盖脸地砸在我们的车上。一想到上游那危若垒卵的沙石大坝在巨大的水压下随时都有垮蹋的可能,我们觉得这大滴大滴的雨水简直就是我们的催命符。河谷里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摇晃着从我们对面开来,车上坐满了撤离的难民,肯定是因为失去了家园,每个人脸上表情呆滞,那麻木的眼神向河谷中张望,那里曾经有他们的家。当卡车和我们擦肩而过时,一位阿加拉(藏语:大妈大婶)注视着我们这几辆张牙舞爪的越野车,突然转动起手中的经筒,那神情分明是在向菩萨为我们的命运祈祷。”
通麦桥到了,由于交通已基本断绝,桥上空荡荡的,桥头矗立着一块用水泥砌的石碑,血红色的碑体上书写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永垂不朽。”特有的时代语言告诉我们,那个悲剧一定是发生在30年以前,他们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他们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有谁还能够向我们讲述那个悲壮的故事?
对讲机中传来头车的呼唤:“他妈的,我们正好也是十个人,如果在这儿牺牲了,恐怕连这么块碑也没有。”
车队继续向河谷中行进,路况越来越糟。河谷两边是高耸的山峰,山峰上长满冷杉,再往上,密布的浓云遮没山顶,泥石流的堆积物掩埋了公路。人们在沙土、巨石和树干树支构成的浮土推上,推出了一条临时救援通道,根本就不能用崎岖、颠簸、险阻这些描述路况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条通道,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一条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此刻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沿着这堆巨大无比的群山排泄物表面,上蹿下跳。
当车队拐过一个弯道,高耸入云的群山被撕去了翠绿的衣服,裸露着可怖的青灰色岩体,淤积的泥沙在山谷之间形成了高2000多米,方圆数公里的天然堤坝。易贡河水陡涨,大堤后面出现了一个面积几十平方公里,深千米的大湖,浩淼的湖水夹带着无穷的能量,不停地冲击着松松垮垮的大堤。几辆工程车在堤坝上忙碌,周围出现了橄榄绿的颜色,他们是武警水电部队的,长年转战在川藏线的深山老林之中。现在,他们的任务是在这座泥石流堤坝崩塌之前,抢挖出一条导流明渠,尽可能地将淤积的湖水泻掉一部分,降低灾难的损失程度。
远远的走过来一个军官,中尉军衔,二十多岁的模样,一聊才知道,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刚大学毕业,学的是水力工程。
“喝点水赶快上路吧,这大坝很危险,翻到大坝上游就安全了。”
“你们不怕嘛?”我问。
“怎么不怕,习惯了。再说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命令,命令让你撤你就撤,不让你撤死在哪都是一样的。我是怕我们这些战士一年四季,整天在大山里转来转去的,很少能见到个人,挺烦的。一见到你们别提多亲了,聊起来没完,一但发生险情,误了你们的大事。”中尉笑着回答。
和战士们告别了,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进。
辛诚抽着烟,他那只夹烟的手微微抖动,眼角有些湿润。
“后来呢?”看他久久无语,我问。
“听说几天以后,导流明渠终于挖好了,但是,在泄水的过程中大坝崩溃了,洪水和泥石流荡涤了易贡河下游的一切,就连那座有着血红石碑的易贡大桥,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了。”说着,辛诚喷出一口浓浓的烟,浓烟幻化成各种形状,袅袅升腾,辛诚呆呆地注视着渐渐消散的烟雾,似乎是想从中寻找到答案……
《交通世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