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几起酒后驾车引发的血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严打酒后驾车运动——而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如何处置醉驾的官员”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番禺某镇那个酒驾被查时称“醉驾是工作需要”的纪委书记就成了焦点。媒体调查发现,梁某19日晚被查,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警方解释称等抽血结果后再拘并无不妥。公众则质疑“这样做会给醉驾者逃脱惩处的机会”,省交管局有关人士也表示“不应该放回去”。
警方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正如公众所质疑,如果逮住的是个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人,这样做醉驾者很容易就逃脱了。而且依据相关法律,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这样看,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显然有袒护之嫌。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既伤害了严打醉驾运动的公信力,也容易使本是醉驾问题转为官民矛盾。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原罪和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而不是民众与官员、强者与弱者的矛盾。公众的“敌人”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可是,如果执法者在治理运动中不能公正执法,不能严守程序、严格执法、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偏袒了公众深恶痛绝的特权群体,哪怕仅仅在程序上有一点儿瑕疵,执法时有一点儿偏向,都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
官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如果权大于法,权力常常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律捏在手上随意揉捏。平民违法必究,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这正是法律缺乏公信的制度根源——这种现实语境中,公众便对“公正执法”充满怀疑,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于是,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治理运动中,舆论的眼睛总会本能地紧盯着官员群体,很自然地将“能否一视同仁地严惩官员”视作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以“有罪推定”的逻辑苛求地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
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把柄,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会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邓玉娇案是这样,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照常上班”(平民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显然也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而指向官官相护,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就这样演化成了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转化,既使治理酒驾运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又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治理:官员违法受到袒护,我们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人们沉浸于这样的想象中,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
理性的执法者,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这种情绪,知道对权力充满不信任的公众这时候会紧盯着官员群体,等着从执法细节中寻找程序瑕疵——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越是涉及到官员的案例,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严厉执法,透明公开,一视同仁,绝不护短,借此向公众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心,消除公众的疑惑。否则像番禺警方这样的话,只能使醉驾问题转为官民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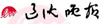








![[车春秋]成品油价格再次上调](http://i1.itc.cn/20101222/29e_a9dd0c61_1984_4e01_84af_f99c33103082_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