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无愧于“万国汽车博览”的称号,然而,直至旧中国的历史终结,上海街头一直由洋车独占着天下,中国人岂能高兴得起来?
也许,这更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中国人不是没想到过自己造车。1920年,民族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就已提出,要发展交通、修筑大路(公路)及建立自动车(汽车)工业。
之后,为了一圆中国人的造车梦,先辈们从未中断过努力。而上海正是这个梦工场的大本营。
第一辆由中国人自制的汽车,其实诞生于东北沈阳。1929年8月,沈阳迫击炮厂附属民生工厂获得张学良将军资助,请来美国人迈尔斯当总工程师,带领200多名员工边学边干,开始自己造车。造车的蓝本是一辆美国“瑞雷号”汽车,他们将瑞雷号“开肠破肚”进行拆卸、测绘,逐件研究、设计,整整苦干了近两年时间。1931年5月,终于造出一辆2吨载重货车,取名“民生牌”。
这辆在东北沈阳诞生的汽车,却成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1931年9月12日,“民生”牌汽车千里跋涉开进大上海,参加在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新建会场举行的中国首次路市展览会。当这辆中国自产载货车出现在展台时,全场立刻响起了阵阵喝彩。
中国人也能造汽车了!是中国人,都为这一刻而感到扬眉吐气。
但这是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不多几天,东北便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一个噩耗传遍路市展览会:生产民生牌汽车的民生工厂已经落入日寇的魔掌!展会上寒风顿起,但回望展台,民生汽车却依然光艳夺目。人们暗暗庆幸:民生汽车逃过这一生死之劫,也就为中华民族的汽车工业保住了第一颗种子。
9月29日,路市展举行声势浩大的汽车游行,当日彩旗飘舞的游行队伍中,60多辆中外参展车排成一字长蛇阵缓缓而行,“中国造”民生牌汽车作为前导车昂然走在最前列,显得格外神采斐然。以后,这辆民生汽车便归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所有,长期落籍于上海,1936年被改装为“民生号”游览车继续为社会服务。
自民生汽车开风气之先,中国大地上的“造车热”便一发而不可收。而最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是上海制造的第一辆汽车——“本茨式中国号”柴油机汽车。
国内实业界一些重量级人物,对中国道路上只有外国车招摇过市早就愤愤不平,决意自己筹资来建厂造车。1936年秋天,由中国银行出面牵头,在上海虎丘路会集众多实业界人士,以官商合办、个人入股形式成立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筹备处。随后在南京国货银行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公司正式诞生。
造车自己没有经验,就走中外合作造车的路。1936年,筹建中的中国汽车公司就已派出专家出国考察,同年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由奔驰汽车厂派出以主任工程师冯格腾为首的20名专家来华协助建厂。合同期间,奔驰汽车厂将向该公司提供7000辆载重2.5吨的柴油机汽车散件,在中国组装整车。
1937年,中国汽车公司在上海半淞园路建成上海分厂,专门组装2.5吨柴油机汽车。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柴油、汽油都靠国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技术顾问冯格腾经过四处考察,大胆提议改用植物油作燃料。
这年3月,第一辆“本茨式中国号”柴油机汽车在上海装配成功,车的标志为中字外加一个圆圈,所以又称“中圆牌”。
“中国号”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纪录。4月1日,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着“中国号”从上海出发,一路跋山涉水行驶近一个月,抵达昆明参加京滇(南京—昆明)公路周览会。据当时记载,“中国号”沿途分别采用花生油、菜籽油、茶油、桐油、棉籽油、烟籽油为燃料,居然效果不错,平地每加仑可行23.4公里,山区每加仑也可行至12.5公里,而且途中从未发生过一起故障。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彻底打破了中国人的造车梦。到上海沦陷之日为止,上海分厂总共只组装了近百辆汽车,以后几经辗转,便就此销声匿迹。
1937年,几乎在半淞园路挂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上海分厂”招牌的同一时刻,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将一台自己研制的柴油机装上汽车,也在沪杭线上举行首次试行。如果比喻中国汽车公司是一支集团军,这位中年人加入的队伍,便是地方小股部队。在上海最初的造车史上,造车“游击队”也纷纷“揭竿而起”,大多从攻克发动机起步投入“造车运动”。
这位中年“游击队员”名叫支秉渊,浙江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曾获得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31年“九·一八”以后,担任电气工程师的他独立创办了上海新中工程公司,在闸北建厂研制柴油发动机。第二年试制成功第一台国产柴油发动机,翌年将这台自制柴油机装上汽车,在沪杭线上举行了首次试行。虽然返程途中发动机一度发生故障,但总体而言行驶还较顺利,故障经回厂检修排除后,发动机又恢复了正常。然而它无法排除时代所造成的“故障”,以后落得与“中国号”几乎一样的命运。
上海造车运动,一条更长的战线是对代燃汽车的研究、试制。当时中国是个“贫油国”,汽油都只能依赖外国进口,每年流出去的外汇多得惊人。一些爱国技术专家苦心求索,寻找到一条出路:寻求汽油的代用品,研制代燃汽车。
汤仲明是第一个独立研制煤气发生炉的专家。1926年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归国后,就一心投入研制以木炭为燃料的煤气发生炉。1931年初战告捷,试制成功1台“木炭代油炉”,以后分赴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进行表演,曾受到南京政府当局的表彰。1935年汤仲明南下至上海,在齐齐哈尔路270号创办了“仲明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自设工场制造煤气化油炉,并推广到江浙和广西、江西等地。1936年他用1辆四缸福特汽车改装试制成煤气发生炉汽车,冬天在上海附近作5000公里的长途试车,证明效果良好,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还试坐过这辆车。1937年春试制成第二辆,由上海开至南京,于佑任、居正等民国元老也曾兴致盎然地登车试坐。后又用6辆大蒙天汽车改装投入运行。上海的沪太、锡沪两家长途汽车公司也将部分车辆进行改装使用,锡沪公司近一年中先后装配28辆煤气车投入使用,8个月内净赚了5800多元。不久“八·一三”战火打碎了汤仲明的造车梦。
另一个名叫张登义的工程师,也很早开始潜心研究代燃车。1933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5省市交通委员会成立,麾下设有煤气车试验委员会,张登义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当时煤气车委员会就向法国、瑞典各进口了2套煤气代燃炉。张登义与一些专家经过装车反复试验,在上海用法国进口的下吸式煤气代燃炉改装成1辆大蒙天底盘和发动机的木炭代燃车。1936年张登义出任上海公用局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一度他将老西门至龙华的1路公共汽车全部改装为木炭代燃车,代燃汽车由此进入了实际应用阶段。但由于使用时间并不很长,所谓进入实用阶段,也多半只是象征性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一群志同道合的技术人员——向恺、向德、张秉章、向慷等人一起筹资10万元,在上海成立了“中华煤气车制造无限公司”,埋头致力于经营制造各种煤气炉、煤气引擎及煤气发生炉。他们自行设计制造的22—A型煤气发生炉,经过装车试验证明,该代燃车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38英里(合61.14公里),每磅木炭可行驶0.923英里(合1.49公里),只是在冷炉生火时需要用少量汽油以启动发动机。当时的军政部交通司曾制有计划,从1935年起用这种煤气发生炉分批改装辎重兵团的军用汽车,但后来似乎也就没有了下文。
中国人的“造车梦”尽管缤纷灿烂,令人着迷,但时代已经决定了它的命运:梦,终究还是梦,而从未成为真正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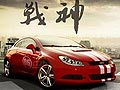



![[车春秋]成品油价格再次上调](http://i1.itc.cn/20101222/29e_a9dd0c61_1984_4e01_84af_f99c33103082_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