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麻将之城
文 路胥
第六代导演王光利最近拍了《血战到底》,讲的就是黑色幽默成都人的一则故事。
“血战到底”是成都麻将的一种特殊玩法。成都人爱喜新厌旧,善于在平淡中找刺激。“推到和”、“打缺”、“唱歌跳舞”、“勇往直前”、甚至“血流成河”,你都不清楚这样的名词是怎么从第一张麻将桌开始传遍全城的。成都可是有过千万的人口,你也根本无从推敲,不需要现代媒体手段,没有“麻将协会”推广,也不清楚谁制定了规则,它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呼啦啦从大慈寺茶馆的麻将桌传到农家乐的麻将桌上,从宽窄巷子内里的麻将桌传到了黄龙溪的麻将桌。
似乎只有摸着密胺质感的麻将,成都人心里才有底气。汶川地震后,成都人被赶到了大街上,刚通好电呢,成都人就搬来四方桌,在夜灯下打牌了。成都人说打牌,基本不是指扑克,而是麻将。地震了,什么都可以停下,唯独有麻将的生活不能停下。老美一有灾难,心理医生必要赶赴前线。对成都人来说,麻将就是心理医生。摸着滑溜溜的麻将,表明生活一直在延续,领导骂几句,孩子不争气,两口子怄气,都抛到青城山外去。或者说,如果没有麻将,成都人将丧失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而只有两手与滑滑的麻将互相安慰一番,他们才可以将心里的闷气、鸟气、闲气给倒个精光。
眼耳鼻舌身,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用五种感官都对城市摸索了一遍,而一般人是很少留意触摸对于生活的含义。成都人则不,他们将身体的触感发挥到极致。全城皆麻不算,到了夏天,你到成都虹口,看成都人是怎么玩麻将的,你就知道成都人多么会照顾自己:他们将方桌子竹椅子摆到浅河滩里,四个脚泡在凉飕飕滑溜溜的水里,手里摸着温香软玉般的牌,蚊子不敢来,清风耳鬓过,就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打麻将牌了。两边是可以照顾舌头的农家乐,河里是密密麻麻的打麻将的人,如此浩浩荡荡的场面,只能用蔚为壮观来形容。
神人可以撒豆成兵,成都则是撒麻成城。
城里的茶馆自不去说它。成都人自创了一种气象名词叫“喝茶天”,一看那云天正合意,就出来泡茶馆了,泡茶馆十有八九也就是打麻将了,文雅的“喝茶天”就变成了市民的“麻将天”。来成都投资建厂的外地老板,聪明的就会在厂里设一个文化娱乐中心,就是放几台自动麻将桌,下了班老板工人一起上。如果郭台铭到成都的工厂考察下,估计富士康也不会出那么多晦气事。
成都人说出城去玩,大致也不过是换个地方打麻将而已。农家乐、风景区、度假村、游船上,去的是名胜古迹,名为游山玩水,实则是摸九条三筒。甚至有的人出国,也就是开一旅馆打麻将,昏天暗地玩几天,从伦敦、巴黎回来了,还在叹息“曾经在我面前有一个做‘暗对七’的机会,可惜我错过了”。
在成都,还有两种场合是打麻将的天堂。一是婚礼,二是葬礼。尤其是葬礼,通常叫“打丧伙”,比婚礼麻将更热闹。死者家属要守灵,所谓守灵,就是和亲朋好友打麻将。“红白喜事”也是民间传统,在丧期打麻将,或者是庄子“击缶而歌”的潜流在成都平原给保留下来了。
春天阳光媚好,成都人就坐在粉红的桃花树底下,甜白的梨花树底下,快快乐乐地打;夏天果子飘香,他们就坐在阴凉的农舍中,坐在沁凉的河水中,不亦乐乎地打;秋天云淡风轻,就坐在街道两边,坐在绿荫道上,劲头十足地打;冬天寒风乍起,就搬到开着暖气的室内,昼夜不分地打。
你去听听《血战到底》里的插曲,就知道什么叫成都麻将:娃你不要吵,娃你不要闹,反正今天没的事我陪你不睡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没看过这本书,我一直猜测这可能是写触麻成瘾的成都市民吧。
|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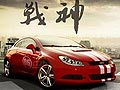


![[车春秋]成品油价格再次上调](http://i1.itc.cn/20101222/29e_a9dd0c61_1984_4e01_84af_f99c33103082_0.jpg)













